内容摘要
在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中,“希腊化”与“伊朗性”的关系表现出先合后分的阶段性特征。“希腊化”是帕提亚帝国前期体现出的表层文化,而“伊朗性”是帕提亚人自身文化中始终延续并且逐渐凸显的本体文化。“伊朗性”体现在帕提亚帝国的钱币、图像、铭文、建筑和王权观念等诸多方面。在帕提亚帝国前期,出于巩固统治的政治需要,“希腊化”与“伊朗性”之间呈现出融合并存的态势。帕提亚帝国后期,随着罗马—帕提亚两极格局对立形势的到来,帕提亚人逐渐走向去希腊化和全面复兴伊朗文化。从持续时间和文化性质来看,“伊朗性”应是理解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和文明交往特征最重要的维度。帕提亚文化对中古伊朗文明和罗马帝国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价值不应被其表面的“希腊化”和“内亚性”特征所遮蔽。
关 键 词
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伊朗性;希腊化;内亚性
作者简介
龙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后。
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多卷本)子课题“新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以及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罗马波斯战争与古代晚期中东文明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全文如下:
目前学界似乎认为,帕提亚帝国自始至终都受到了希腊文化的深度影响,其主流文化特征是希腊化文化。但帕提亚帝国同样也是古代伊朗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帕提亚帝国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帝国之间的渊源和承继关系,揭示帕提亚帝国对中古波斯文明发展所起到的贡献与作用,是当今帕提亚史研究尚未深入的地方,尤其是随着当今考古学、钱币学和伊朗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帕提亚史研究的议题开始逐渐走向多元化。本世纪初,国外伊朗学界对帕提亚史的研究出现了奥布里希特、拉西姆·沙耶甘、帕尔瓦内赫·博沙利亚提和尼科劳斯·奥弗图姆等代表人物。其中,拉西姆·沙耶甘综合利用古典史料、近东楔文史料和古代伊朗铭文对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政治宣传中的复兴阿契美尼德波斯传统现象进行了独到而深刻的研究;帕尔瓦内赫·博沙利亚提的萨珊—帕提亚贵族联盟(Sasanian-Parthian Confederacy)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帕提亚—萨珊时期伊朗历史的连续性;奥布里希特在其新著《早期帕提亚史》中综合利用古典学、考古学和伊朗学成果对早期帕提亚政治史、帕提亚帝国与中亚草原游牧文化关系等问题多有新见。总体来看,虽然学界对帕提亚帝国的研究已经涉及政治、经济、艺术等诸多领域,但帕提亚史研究的进一步突破还需要对制度、宗教和族群认同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实现。
已故德黑兰大学教授扎林库伯曾认为:“竭力保持希腊化与东方化两种因素的平衡是阿什康尼王朝(即帕提亚帝国)的基本特征”,而帕提亚王朝的建立是“伊朗的生命力对希腊人统治和希腊化的反驳”,他对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的判断虽为至论,但他似乎也陷入了将“希腊化”和“伊朗性”两大文化因素对立处理的传统思维方式。笔者认为,帕提亚研究“希腊化范式”主要的局限性在于,由于过于强调希腊文化对帕提亚帝国的单向影响,因此难以揭示帕提亚帝国自身的核心文化属性。伊朗民族主义史观则把“伊朗性”与“希腊化”对立起来,同样导致了帕提亚史叙事方式的二元割裂。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帕提亚帝国“伊朗性”的一面要么被“希腊化”范式遮蔽,要么与“希腊化”范式形成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可以说,希腊文化单向传播论和希腊—伊朗文明不可融合论共同导致了当今帕提亚史研究的困境。只有站在古代伊朗自身历史发展的主客观环境条件下来研究帕提亚史,才能够更加准确全面地揭示帕提亚帝国多元文化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帕提亚帝国的文化属性而言,厘清“希腊性”“内亚性”和“伊朗性”所占的比重以及三者之间的“体用关系”尤为重要。本文拟通过对帕提亚帝国全时段文明交往特征的考察,在重新认识帕提亚帝国“希腊性”和“内亚性”的表现及深度的基础上,着力探讨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中的“伊朗性”文化特征及其内涵、外延,以图揭示帕提亚帝国的核心文化属性和帕提亚帝国时期伊朗文明发展的整体趋势。
一、帕提亚帝国的希腊化表象与伊朗性本质
学界认为,帕提亚帝国“希腊化”的主要依据是,从米特里达梯一世(Mithridates I,前171~前138年在位)开始的帕提亚诸王钱币上几乎均有“爱希腊”(ΦΙΛΕΛΛΕΝΟΣ,Philhellene)的铭文。帕提亚帝国在米特里达梯一世时期扩张至两河流域后,面对当地众多希腊化城市,帕提亚诸王在钱币上标榜对希腊文化的仰慕以笼络被征服的塞琉古帝国属地,对帕提亚帝国巩固新征服地区的秩序而言确有必要。以托勒密、塞琉古和安提柯王朝为代表的希腊化王朝,由于本身统治族群为希腊—马其顿裔,无须在钱币上证明自己“爱希腊”。帕提亚帝国的“爱希腊”钱币特征不符合希腊化王朝钱币传统,实际上是帕提亚人为减轻自己统治希腊化地区的阻力有意为之。帕提亚帝国的“爱希腊”口号从反面充分体现出自己族群乃至文化出身的“非希腊性”。从公元1世纪初阿塔巴努斯二世(Artabanus II,10~38年在位)开始,帕提亚帝国君主发行的钱币不再出现“爱希腊”铭文。因此,“爱希腊”对帕提亚帝国统治的维持并非始终是不可或缺的政治口号,而是可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恢复或撤销的,它只存在于公元前141年至公元12年的早期帕提亚帝国阶段。帕提亚帝国的官方“爱希腊”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在帝国早期扩张阶段,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而选择的策略,这种“爱希腊”并不带有更多心理和情感上的仰慕。
学界在强调帕提亚帝国“希腊化特征”的同时,也强调过帕提亚人的“斯基泰渊源”,草原斯基泰文化代表的“内亚性”是解读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的又一主要视角。从帕提亚君主发行的钱币以及古典作家的记载来看,草原游牧文化的一些表层因素确实对帕提亚帝国产生了影响,集中表现在帕提亚人的骑射风俗上面。早期学者认为,帕提亚开国君主阿萨西斯一世(Arsaces I,前247~前211年在位)的钱币正面为头戴巴什里克帽(Bashlyk)的国王侧面像,这种尖帽应该是由斯基泰式尖帽演化而来。另一个帕提亚帝国“内亚性”的表现是,帕提亚钱币的反面经常可见到右手持弓的国王侧面坐像。从表面上看,阿萨西斯一世钱币上的巴什里克帽和复合弓是帕提亚艺术受到斯基泰草原艺术影响的直接体现,宣示出帕提亚人的游牧文化特色。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早期帕提亚君主头戴的软帽并非斯基泰人常见的护耳毡帽,与斯基泰贵族流行的高耸尖帽之间更有巨大的差距,而应是波斯帝国行省总督铸币像中极其常见的护耳软帽(Kyrbasia),因此早期帕提亚钱币上的国王服饰特征反映的正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铸币传统和波斯人的服饰特色。
英国学者库尔提斯指出,帕提亚钱币上的持弓坐像源自波斯传统,因为这一持弓坐像与阿契美尼德王朝西部总督发行的钱币背面持弓坐像极为类似。显然早期帕提亚诸王便知晓波斯铸币传统,因而直接模仿了过来。而米特里达梯一世之后帕提亚诸王钱币背面出现的希腊城市女神狄科(Tyche)右手托举胜利女神(Nike)的图像,可以解读为伊朗王权灵光神(Farr)将统治合法性赐予帕提亚君主的象征,希腊城市女神Tyche其实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灵光神的希腊化呈现(Hellenistic Interpretation)。如果对帕提亚钱币进行全时段考察,会发现公元前2世纪帕提亚钱币背面的狄科女神坐像到公元前1世纪后又逐渐重新回到国王右手持弓坐像,如奥罗德一世钱币和帕提亚末王阿塔巴努斯四世钱币。因此,体现希腊—伊朗宗教混同趋势的“阿波罗—密特拉持弓坐像”是帕提亚钱币的重要特色。这个特色的内涵并不一定指向希腊文化,很可能是用希腊的方式表达伊朗的思想。实际上,帕提亚时期伊朗人对希腊神形象的理解往往会发生“伊朗化”,如考古学者发现于贝希斯敦山岩上的赫拉克勒斯雕像,在伊朗文化语境下应该被解读为琐罗亚斯德教的胜利战神维瑞斯拉格纳(Verethragna)。从钱币上看,帕提亚钱币的希腊化特征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消退的同时,愈益表现出“伊朗性”。自弗拉特斯一世(Phraates I,前176~171年在位)起,帕提亚诸王钱币上国王头像由希腊式的无须洁面特征转变为典型的波斯式颗粒状发体,脸部轮廓也从希腊式的柔和俊朗演变为波斯式的钩鼻深目。从阿塔巴努斯一世(Artabanus I,前127~前124年在位)起,帕提亚钱币上国王不再身穿希腊式外套(Chiton),而是改穿波斯式的环片铁甲;继阿塔巴努斯一世之后,米特里达梯二世(Mithridates II,前123~前87年在位)以来的帕提亚钱币又进一步凸显其东方伊朗式王权传统的形象特征:国王侧面像开始蓄长须、戴护耳高圆顶王冠(Kolah),耳后下垂波浪形珍珠式发体,呈现出典型的帕提亚“三分式”发型,彰显出帕提亚人逐渐抛弃希腊化传统向伊朗传统回归。由此可见,帕提亚钱币的希腊化特征并不持久,来自阿契美尼德王朝铸币传统的伊朗特色才是帕提亚钱币图像终极的核心特征。
帕提亚帝国的“内亚性”常被理解为对斯基泰草原游牧战术的单纯喜好。从军事体系来看,帕提亚帝国的确受草原游牧人骑兵战术的深刻影响。但帕提亚帝国还拥有自成一格的重装骑兵传统,帕提亚人的具装重骑兵被希腊人和罗马人分别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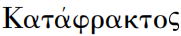 ”和“Clibanarii”,其含义分别为“全身包裹的”和“火炉人”,一般翻译作铁甲骑兵,这是亚洲最早出现的甲骑具装。罗马史家查士丁对帕提亚铁甲骑兵的装备有着详尽的描述:“他们的铠甲由一片片互相叠置的环片金属制成,就像鸟的羽毛一样同时覆盖骑手和战马全身。”帕提亚人能够发展重装骑兵,与伊朗高原能够产出体格高大、载重能力强的战马密不可分。从米底山区牧场培育的尼西安战马(Nisean Chargers,旧译“尼萨马”)是米底人、波斯人和帕提亚人均青睐的重装骑兵战马。因此,至少从马种培育来看,波斯本土的重装骑兵与斯基泰人的军事传统应没有直接关系,应被视作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自身延续下来的传统。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阿契美尼德王朝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已经开始驯养尼西安战马;斯特拉波也提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人在米底常年维持着5万匹母马的培育规模,并指出这些马现在叫做“帕提亚马”。帕提亚帝国军事体系的特点在于,其武装力量几乎全部由铁甲骑兵和弓骑兵构成,其兵源分别来自帕提亚上层大贵族和依附于大贵族的低阶帕提亚小贵族及自由民,这一军事体系实际上是对波斯传统和斯基泰传统的一种综合,而非对斯基泰军事体系的简单复制。
帕提亚帝国“希腊化”的另一个证据是,卡莱战役后帕提亚人将克拉苏的首级用作表演欧里庇得斯悲剧《酒神的伴侣》的道具。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帕提亚人在战后将克拉苏的首级割下作为与亚美尼亚国王观赏该剧的实体道具,后又以融化的黄金灌入克拉苏的喉咙以讽刺其贪婪。帕提亚上层精英熟悉希腊文化,观看希腊戏剧,这似乎是帕提亚人希腊化的明证。希腊文化中的流行元素出现于这一时期东方君主的宫廷是极为常见的现象,而希腊化程度的标尺应该是东方族群希腊语人名的普及程度,如希腊化程度较高的犹太哈斯蒙尼王朝(Hasmonean Dynasty)君主采用“亚历山大”“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安提柯(Antigonus)”这样的希腊式人名。反观帕提亚人没有任何君主采用希腊式的人名,都是清一色的伊朗语人名,如阿萨西斯(Arsaces/Arshaka)、米特里达梯(Mithridates/Mehrdad)、弗拉特斯(Phraates/Farhad)等。因此,观看戏剧只能证明帕提亚上层社会接受了希腊文化的某些因素,但不能证明普通帕提亚人在族群认同的深层次上接受了希腊文化。
以“内亚”视角解读帕提亚人对克拉苏首级的处置方式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帕提亚人并没有将克拉苏的首级作为“酒器”使用,这一举动与传统的草原游牧贵族处置战败者的风俗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小的距离。我们在解读帕提亚人对克拉苏首级的处置方式时,应该注意到以融化的黄金灌入克拉苏喉咙这一情节的伊朗文化背景。盖因这种处刑方式非常吻合琐罗亚斯德教的末日审判和罪罚观念,也被萨珊王朝沿袭于对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的处置方式:根据4世纪的基督教作家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的记载,在埃德萨战役中被俘的罗马皇帝瓦勒良在波斯的结局极为凄惨,即“被波斯人灌入融化黄金后剥皮实草并献祭于波斯火庙”。萨珊波斯人对战败被俘罗马皇帝的处刑方式与帕提亚人对克拉苏首级的处置方式有一个核心共同之处,即以融化的金属对被惩罚的对象施刑,而中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律法也有“烧铁灼舌”判定罪犯是否说谎的记载。因此,从对克拉苏的处置方式这一历史情节来看,帕提亚帝国对伊朗文化的传承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层面。对琐罗亚斯德教律法仪轨的传承并非是萨珊波斯人刻意“复兴”的结果,而是奠基于阿契美尼德王朝以来波斯文化的发展及其在帕提亚帝国时期的延续。由此可见,以琐罗亚斯德教为代表的波斯文明因素在帕提亚帝国时期并没有发生“断裂”,而是得到了相当深度的传承和发展。
由上可知,帕提亚帝国的“希腊化”特征,通常是表达伊朗宗教文化的图像手段,而帕提亚帝国看似明显的“内亚性”,其本质特征仍然是由波斯骑兵传统和琐罗亚斯德教文化构成的“伊朗性”。因此,不管是“希腊化”还是“内亚性”,都只触及到了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的表层。帕提亚帝国在文化属性的本质特征“伊朗性”,由于部分采取了“希腊化”和“内亚性”的表达方式,而难以被直接察觉。这一方面说明了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帕提亚帝国的“伊朗性”在前期是能够包容“希腊化”和“内亚性”的。只有理解了帕提亚帝国的“伊朗性”,才能看清帕提亚人多元文化属性与其主流文化底色之间的辩证关系。
”和“Clibanarii”,其含义分别为“全身包裹的”和“火炉人”,一般翻译作铁甲骑兵,这是亚洲最早出现的甲骑具装。罗马史家查士丁对帕提亚铁甲骑兵的装备有着详尽的描述:“他们的铠甲由一片片互相叠置的环片金属制成,就像鸟的羽毛一样同时覆盖骑手和战马全身。”帕提亚人能够发展重装骑兵,与伊朗高原能够产出体格高大、载重能力强的战马密不可分。从米底山区牧场培育的尼西安战马(Nisean Chargers,旧译“尼萨马”)是米底人、波斯人和帕提亚人均青睐的重装骑兵战马。因此,至少从马种培育来看,波斯本土的重装骑兵与斯基泰人的军事传统应没有直接关系,应被视作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自身延续下来的传统。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阿契美尼德王朝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已经开始驯养尼西安战马;斯特拉波也提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人在米底常年维持着5万匹母马的培育规模,并指出这些马现在叫做“帕提亚马”。帕提亚帝国军事体系的特点在于,其武装力量几乎全部由铁甲骑兵和弓骑兵构成,其兵源分别来自帕提亚上层大贵族和依附于大贵族的低阶帕提亚小贵族及自由民,这一军事体系实际上是对波斯传统和斯基泰传统的一种综合,而非对斯基泰军事体系的简单复制。
帕提亚帝国“希腊化”的另一个证据是,卡莱战役后帕提亚人将克拉苏的首级用作表演欧里庇得斯悲剧《酒神的伴侣》的道具。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帕提亚人在战后将克拉苏的首级割下作为与亚美尼亚国王观赏该剧的实体道具,后又以融化的黄金灌入克拉苏的喉咙以讽刺其贪婪。帕提亚上层精英熟悉希腊文化,观看希腊戏剧,这似乎是帕提亚人希腊化的明证。希腊文化中的流行元素出现于这一时期东方君主的宫廷是极为常见的现象,而希腊化程度的标尺应该是东方族群希腊语人名的普及程度,如希腊化程度较高的犹太哈斯蒙尼王朝(Hasmonean Dynasty)君主采用“亚历山大”“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安提柯(Antigonus)”这样的希腊式人名。反观帕提亚人没有任何君主采用希腊式的人名,都是清一色的伊朗语人名,如阿萨西斯(Arsaces/Arshaka)、米特里达梯(Mithridates/Mehrdad)、弗拉特斯(Phraates/Farhad)等。因此,观看戏剧只能证明帕提亚上层社会接受了希腊文化的某些因素,但不能证明普通帕提亚人在族群认同的深层次上接受了希腊文化。
以“内亚”视角解读帕提亚人对克拉苏首级的处置方式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帕提亚人并没有将克拉苏的首级作为“酒器”使用,这一举动与传统的草原游牧贵族处置战败者的风俗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小的距离。我们在解读帕提亚人对克拉苏首级的处置方式时,应该注意到以融化的黄金灌入克拉苏喉咙这一情节的伊朗文化背景。盖因这种处刑方式非常吻合琐罗亚斯德教的末日审判和罪罚观念,也被萨珊王朝沿袭于对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的处置方式:根据4世纪的基督教作家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的记载,在埃德萨战役中被俘的罗马皇帝瓦勒良在波斯的结局极为凄惨,即“被波斯人灌入融化黄金后剥皮实草并献祭于波斯火庙”。萨珊波斯人对战败被俘罗马皇帝的处刑方式与帕提亚人对克拉苏首级的处置方式有一个核心共同之处,即以融化的金属对被惩罚的对象施刑,而中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律法也有“烧铁灼舌”判定罪犯是否说谎的记载。因此,从对克拉苏的处置方式这一历史情节来看,帕提亚帝国对伊朗文化的传承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层面。对琐罗亚斯德教律法仪轨的传承并非是萨珊波斯人刻意“复兴”的结果,而是奠基于阿契美尼德王朝以来波斯文化的发展及其在帕提亚帝国时期的延续。由此可见,以琐罗亚斯德教为代表的波斯文明因素在帕提亚帝国时期并没有发生“断裂”,而是得到了相当深度的传承和发展。
由上可知,帕提亚帝国的“希腊化”特征,通常是表达伊朗宗教文化的图像手段,而帕提亚帝国看似明显的“内亚性”,其本质特征仍然是由波斯骑兵传统和琐罗亚斯德教文化构成的“伊朗性”。因此,不管是“希腊化”还是“内亚性”,都只触及到了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的表层。帕提亚帝国在文化属性的本质特征“伊朗性”,由于部分采取了“希腊化”和“内亚性”的表达方式,而难以被直接察觉。这一方面说明了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帕提亚帝国的“伊朗性”在前期是能够包容“希腊化”和“内亚性”的。只有理解了帕提亚帝国的“伊朗性”,才能看清帕提亚人多元文化属性与其主流文化底色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从城市建设和王权观念看帕提亚帝国的“伊朗性”
如前所述,帕提亚帝国前期的“伊朗性”往往通过“希腊化”和“内亚性”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在许多其他文化特征上可以更加直接地发现帕提亚帝国的“伊朗性”。首先可以发现的是,帕提亚帝国的建城举措和王权观念与希腊化王朝明显有别,并且表现出了鲜明的“伊朗性”。
希腊化文明的维持和传播主要通过新建城市进行,是否继承和推广希腊化王朝的建城理念是观察帕提亚帝国是否深度“希腊化”的重要指标。帕提亚帝国对塞琉古王朝留下的希腊城市虽然不加干预任其自治,但帕提亚人从未将希腊城市作为自己的政治中心,而是有着自己完全独立的城市和首都体系。早期帕提亚国家首都位于里海东岸科佩特山北麓的老尼萨(Old Nisa),随着帕提亚人逐渐向西扩张,赫卡铜皮洛斯(Hecatompylos)和米底的埃克巴坦那(Ecbatana)相继成为帕提亚王室驻跸地。没有固定的首都的确是帕提亚帝国“内亚性”的重要体现,但拥有多个首都以适应不同季节和帝国管理的需要同样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已有的传统。从帕提亚首都的变化可见,前期帕提亚国家的首都没有一座是继承塞琉古王朝的希腊式城市,而都是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就已存在的波斯城市或帕提亚人自己发展起来的都市。随着帕提亚人在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将其领土扩展至东起阿姆河、西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广大地区,帕提亚诸王意识到有必要确立一个稳定的首都,以控制这个帝国辖下的广大地区,帕提亚人最终选择在底格里斯河东岸营建新都泰西封(Ctesiphon)。
帕提亚人建造泰西封与希腊化王朝君主建设希腊式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希腊式城市的建立一般伴随着希腊—马其顿定居者的迁入,这些城市一般具备剧院、体育场、公民大会广场等希腊城邦传统功能建筑。而泰西封的主要人口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当地人群以及逐渐定居于此的王室贵族,其皇宫建设和城区布局看不出典型希腊式城市的风格。考察帕提亚—萨珊帝国近七百年对以泰西封为中心的两河流域城市群的建设和统治历程可以发现,正是泰西封逐渐取代了塞琉西亚作为希腊化时期两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开启了两河流域城市群的去希腊化和波斯化进程。公元前141年,帕提亚军队夺取了塞琉古王朝的东都塞琉西亚。根据老普林尼《自然史》的记载,公元前1世纪时塞琉西亚人口达到60万,可见其规模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东方帝国的首都。然而,帕提亚人并没有顺势将都城移至塞琉西亚,而是在塞琉西亚的底格里斯河东岸驻军监视该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帕提亚人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军营基础上发展成为首都泰西封。从此之后,泰西封迅速崛起并逐渐取代塞琉西亚两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成为帕提亚和萨珊王朝近七百年的统治中心,并发展成以此为中心的大都会城市群,即阿拉伯人所说的“麦达因”(al-Mada’in,意为“诸城”)。
20世纪西方考古学家对泰西封遗址的发掘表明,泰西封是一座以波斯文化为主体的城市,其建筑风格具有明显的东方特色。尤其是奠基于帕提亚时期并成熟于萨珊时期的皇宫正殿塔克·基斯拉(Taq Kisra)拱券,是典型的波斯伊万(Iwan,抛物型拱券)建筑风格。不仅如此,以泰西封为代表的帕提亚城市还逐渐将其艺术风格扩展至帕提亚在两河流域的众多附属王国,如由阿拉伯人建立的位于底格里斯河中游西侧的哈特拉(Hatra),其神庙建筑便受到帕提亚伊万式拱券的强烈影响。公元165年罗马军队彻底焚毁塞琉西亚后,泰西封作为两河流域核心城市的地位彻底稳固。公元3世纪萨珊帝国崛起后,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224~240年在位)更将塞琉西亚旧址按照波斯风格重建为“韦赫—阿尔达希尔”(Veh-Ardashir)。尽管在同时期罗马—拜占庭文献对萨珊帝国首都的称谓中,仍然保留了“塞琉西亚—泰西封”(Seleucia-Ctesiphon)的双城名号,但这时的“塞琉西亚”早已不是希腊化时期的塞琉西亚了。因此,帕提亚时期以泰西封为代表的波斯式城市的出现,为萨珊帝国时期波斯式城市在两河流域南部和伊朗高原地区的爆炸式增长奠定了基础。由此可以看出,波斯式城市的建设是帕提亚和萨珊统治者推动去希腊化进程的重要战略举措。泰西封实际上可称为希腊化时期中东地区出现的第一座代表波斯文明的都会型城市,充分体现了帕提亚帝国的“伊朗性”。
除首都选址和建设外,帕提亚帝国的“伊朗性”还体现在对由古代西亚传统王号发展而来的波斯君主专属称号——“王中之王”(ΒΑΣΙΛΕΙΟΣ ΒΑΣΙΛΕΙΟΝ)——的复兴上。从米特里达梯一世起,帕提亚诸王开始使用“王中之王”的称号,并在米特里达梯二世以后开始频繁使用。其实,“王中之王”的本意并非指统治着许多附属国王的最高国王,而是指“我的父亲、我的父亲的父亲……都是国王,所以我也是国王”。正如大流士一世在贝希斯敦铭文中说的:“我,大流士,伟大的国王,王中之王,波斯之王,诸国之王,叙斯塔斯佩斯之子,阿尔萨米斯之孙,阿契美尼德家族中人”,亚美尼亚凡城出土的薛西斯一世铭文所说的:“我,薛西斯,伟大的国王,王中之王,操不同语言的诸省之王,大地所及之王,阿契美尼德家族大流士国王之子。”概言之,“王中之王”称号凸显的是西亚王权自古以来强调父系血缘继承关系的特色,即有着强烈西亚特色的“传统型权威”。而塞琉古君主更多地采用“大王(ΒΑΣΙΛΕΙΟΣ ΜΕΓΑΝΟΥ)”称号,始终不愿接纳西亚的以“王中之王”为核心符号的王权观念。有学者认为,帕提亚帝国采纳“王中之王”称号的原因是帝国内部有众多的臣属国王,而塞琉古王朝以总督管理行省,帝国治下并无附庸国王,故其君主无需称“王中之王”。但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同样采用行省总督制的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君主采用“王中之王”的称号。因此,帕提亚帝国复兴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王中之王”称号并将之传递给后世伊朗诸帝国,个中缘由当与古代伊朗王权的血统合法性观念有深刻的关联,而非仅仅是帕提亚帝国时期对附属王国进行间接统治的现实需要使然。古代伊朗人将世界设想为由七块大陆(Haft Keshvar)构成,而伊朗人的王国位于最大的中央大陆(Khwaniratha)。因此,古代伊朗君主视自己为地上七大气候带之主(King of the Seven Climes),犹如琐罗亚斯德教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及其六大从神的“七位一体”关系。因此,“王中之王”称号除了体现古代伊朗王权嬗替的血统合法性外,也完美契合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天下世界观念。
因此,帕提亚帝国首先明确回避利用既有希腊式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都,进而选择按照波斯风格在已有希腊式城市附近另建新都。作为帕提亚新都的泰西封,最终成为典型的波斯城市,并在长达七百年的时间里发挥着帝国大都会和波斯文明辐射中心的枢纽作用。帕提亚帝国立足于古代伊朗自居天下之中的世界观,重新恢复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王中之王”称号,实现了波斯王权观念的再次复兴与实践,这也是帕提亚帝国“伊朗性”的突出表现。
三、帕提亚—罗马关系对帕提亚帝国“伊朗性”的塑造
如果说帕提亚帝国前期是主要通过“希腊化”和“内亚性”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伊朗性”的话,那么帕提亚帝国后期则开始直接宣示并对外输出自己的“伊朗性”。而在晚期帕提亚帝国对伊朗传统的复兴过程中,罗马帝国的刺激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在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的早期交往中,罗马人一度将帕提亚作为次等的政权对待,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强势和傲慢姿态。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在西亚初次相遇,时任西里西亚(Cilicia)总督的苏拉以罗马属国规格招待帕提亚使臣奥罗巴祖斯(Orobazus),致使米特里达梯二世以有辱国威为由将奥罗巴祖斯使团全部成员处斩。公元前66年,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三世(Phaates III,前70~前58年在位)派使者至罗马东方全权统帅庞培处商议恢复幼发拉底河作为两国边界,庞培傲慢地以“两国边界应由罗马人的意志来确定”回应。而公元前55年“前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单方面撕毁罗马—帕提亚延续四十年之久的和平友好协定(Foedus Amicitiae)入侵帕提亚,则彻底激怒了帕提亚人。面对罗马共和国在东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帕提亚帝国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应对罗马人在东方的霸权主义作风。加州大学的沙耶甘(M.Rahim Shayegan)认为,传统学者所指出的帕提亚王朝所具有的一系列复兴阿契美尼德王朝政治传统的特征,都是保留阿契美尼德王朝记忆的巴比伦祭司书吏集团和希腊罗马作家对帕提亚帝国进行的主动“唤醒”以及对帕提亚西扩并与罗马爆发冲突的外在“解读”。实际上,帕提亚帝国对阿契美尼德传统的复兴虽然很大程度上是罗马一方主动“构建”和“解读”的结果,但“观念往往会演变为事实,而事实反过来塑造着观念”。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的敌意不仅会诱发罗马一方为“模仿亚历山大”(Imitatio Alexandri)举兵东征,也会反过来强化帕提亚人的波斯正统观念。
近东罗马—帕提亚两极格局确立后,罗马帝国在东方以希腊化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并且大力构建以地中海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文明秩序。为了对抗罗马帝国的压力,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政治遗产开始成为帕提亚帝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伊朗主义”(Iranism)成为帕提亚帝国和罗马帝国交往时采用的重要身份宣示。根据塔西佗的记载,公元1世纪初帕提亚国王阿塔巴努斯二世曾威胁罗马皇帝提比略“直至斯特鲁马河的罗马领土都是帕提亚人应该恢复的居鲁士和亚历山大的帝国版图”。而帕提亚帝国也的确尝试过恢复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黎凡特等东地中海地区的统治:公元前40~前38年,帕提亚军队一度席卷了除推罗外的黎凡特海岸全部地区,甚至还进兵耶路撒冷推翻了罗马人扶植的犹太国王,罗马共和国在东方的统治一时间濒临瓦解。在与帕提亚帝国的交往中,罗马人也逐渐承认了帕提亚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对等地位,这也成为当时罗马史家公认的事实。塔西佗和弗拉维斯·约瑟夫斯就将帕提亚帝国和罗马帝国描述为当时世界上的两大强权(Maxima Imperia)和“太阳下两个最伟大的国家”。至公元3世纪初,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公元211~217年在位)在遣使帕提亚国王阿塔巴努斯四世(Artabanus IV,约208~224年在位)请求与帕提亚公主联姻时,卡拉卡拉在给阿塔巴努斯四世的信中高度肯定了帕提亚和罗马作为世界两大强权的地位,并认为:“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各有所长,两大强权的联姻将使世界上所有民族和部落统一于一个权威之下。”尽管卡拉卡拉的书信被认为是故意挑起帕提亚战争的手段,但这足以表明,罗马帝国从统治者到历史学家均开始认可帕提亚帝国与罗马帝国相对等的大国地位。
最后,公元1世纪后帕提亚帝国在面对罗马帝国的文化渗透和外交干预时,愈益明确表达自己的“伊朗性”,以抵制希腊罗马文化的渗透,并以向罗马帝国大力输出帕提亚文化作为反击手段。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与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四世达成久违的和平协议,弗拉特斯四世同意归还卡莱战役中夺取的罗马军团鹰旗和战俘,同时迎娶奥古斯都送来的意大利女奴穆萨(Musa)为皇后。迎娶穆萨之后,弗拉特斯四世畏惧王室斗争,听从穆萨的建议将自己与其他妃子所生的四个儿子都送到罗马帝国为质,只留下和穆萨所生之子弗拉特斯(Phaates V,公元前2至公元4年在位)为王储。公元前2年,穆萨与弗拉特斯王子合谋毒杀弗拉特斯四世,将自己的儿子扶上王位,并下嫁给儿子弗拉特斯五世,成为帕提亚帝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君主。此番举动立即引起帕提亚举国哗然,导致帕提亚贵族联手于公元4年将弗拉特斯五世和穆萨废黜。过去的学者认为,穆萨母子被推翻的原因在于其伦理上引起帕提亚贵族的反感。但不管是从内亚游牧民族的“父死烝母”还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的“最近亲结婚”(中古波斯语Khowēdodah)传统来看,穆萨母子的行为并无不妥。穆萨母子得罪帕提亚贵族的根源并不在于伦理,而在于女性分享政治权力甚至与男性成为共治君主之传统,不符合古代伊朗政治文化。相反,这样的传统在希腊—马其顿君主中较为多见,尤其是托勒密王朝,其根源在于古代马其顿传统。此后直到公元10年阿塔巴努斯二世即位,帕提亚贵族多次废立亲罗马的帕提亚君主,其原因就是在罗马生活长大的帕提亚王子们过分浸淫希腊罗马文化,与帕提亚人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由于弗拉特斯四世的“罗马化”子孙们均不符合帕提亚贵族的要求,帕提亚贵族最终只能支持帕提亚属国君主出身的阿塔巴努斯二世为王,以续接安息王朝王统。
公元51年继位的沃洛基西斯一世更进一步拉大了帕提亚帝国和希腊罗马文化的距离,推动伊朗文化的复兴。沃洛基西斯一世不仅将其弟扶植为亚美尼亚国王提里达特一世(Tiridates I,51~58,66~88年在位),同时开始对散佚的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进行重新搜集、编订和整理。沃洛基西斯一世不仅通过在钱币上铸以火坛图案来复兴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文化,还通过外交手段推动伊朗文化对罗马帝国的输出。公元66年,经过与罗马皇帝尼禄(Nero,54~68年在位)持续数年的军事较量,沃洛基西斯一世终于以尼禄加冕提里达特为条件垄断了帕提亚帝国对亚美尼亚王位候选人的选择权。自此之后,亚美尼亚国王一直由帕提亚安息王室成员出任,亚美尼亚安息王朝正式建立。不仅如此,提里达特前往罗马城接受尼禄加冕期间,开始了伊朗文化对罗马帝国的全面输出。为了彰显帕提亚传统文化的骑射风俗,提里达特率领多达3000人的帕提亚弓骑兵使团进入罗马帝国境内,而尼禄为招待提里达特使团不惜耗费巨资。根据卡西乌斯·狄奥的记载,提里达特为了尊重琐罗亚斯德教不污染水源的传统,选择走陆路前往罗马城接受尼禄的加冕,由此耗费了9个月的时间。由于提里达特在罗马城期间向尼禄大力宣传源自琐罗亚斯德教的密特拉(Mithra)崇拜并得到尼禄的大力支持,密特拉崇拜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迅速传播于罗马帝国。因此,以沃洛基西斯一世为代表的晚期帕提亚君主不仅成功抵制了希腊罗马文化的渗透,而且有力推动了伊朗文化向罗马帝国等周边文明的输出,由此对罗马帝国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余论:帕提亚帝国“伊朗性”的文明交往意义与价值
帕提亚帝国前期的文化属性,虽然表现为“希腊化”“内亚性”和“伊朗性”三者并举,但在“希腊化”和“内亚性”的表面背后,均可发现帕提亚帝国“伊朗性”的文化本质;而晚期帕提亚帝国则在融合消化“内亚性”、抵制罗马帝国战略扩张和文化输出的基础上全面去希腊化并转向独尊其“伊朗性”的一面。在帕提亚帝国三大文化属性中,“希腊化”虽然是前期帕提亚帝国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帕提亚人对希腊文化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希腊化”的图像、雕塑也可以是帕提亚人表达伊朗宗教文化传统的手段。帕提亚帝国的“内亚性”不仅反映在军事体系上,也反映在其王位继承中兄终弟及传统对父死子继传统的侵蚀上。安息王室各支成员围绕帕提亚王位的长期斗争,也可以归因为来自内亚的横向继承传统的强烈影响。塔西佗曾记载帕提亚人有以马匹祭祀河流的习俗,这可以追溯到琐罗亚斯德教的水神(Tir)崇拜。帕提亚帝国的“内亚性”并不单纯是草原斯基泰文化影响的产物,而是始终受到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文明的规范和塑造。因此,帕提亚帝国的“希腊化”和“内亚性”特征都是为“伊朗性”这一根本文化属性服务的。自帕提亚帝国以后,重装骑兵成为后世伊朗诸王朝的军事主力。而身披全套具装铠甲的骑马武士成为中古以降波斯贵族的标准形象,甲骑具装也成为中古波斯细密画艺术的重要主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帕提亚帝国军事体系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中古波斯贵族文化的内涵,以重装骑兵为主流形象的波斯贵族文化最终成为萨珊帝国“伊朗性”和中古波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探讨帕提亚帝国的“希腊化”和“内亚性”特征时,我们应避免脱离伊朗文明自身发展规律来讨论帕提亚帝国的文化属性。实际上,东伊朗语游牧人与西伊朗语的米底人、波斯人同属古代伊朗文化圈,故中亚伊朗语游牧人的“内亚性”本身也是帕提亚帝国“伊朗性”的组成部分。如扎林库伯所言,“帕提亚人在宗教语言和文化上与东部伊朗人的传统有密切联系。这种传统则是伊朗雅利安人故土(Aryānam Vaejo)时期的遗产,它比米底和波斯传统更久远。”实际上,帕提亚人通过把西部伊朗人已经遗忘的东部伊朗传统重新输入伊朗高原,最终形成了构成中古波斯文化之基础的以贵族勇士文化为核心的帕提亚伊朗文化和艺术流派。帕提亚人通过对自己征战、耕作、游牧、狩猎、聚会和宫廷生活的口头传唱,为萨珊王朝时期波斯诗歌和官方史志《众王之书》(Khwadāy Nāmag)以及后世伊朗民族史诗《列王纪》(Shāhnāmeh)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帕提亚(Pahlav)一词最终在波斯语里衍生出勇士、贵族、冠军等含义。可以说,中古波斯贵族社会的形成正式奠基于帕提亚时期。因此,从长时段历史发展来看,帕提亚帝国的“伊朗性”,可以归纳为帕提亚帝国自身的伊朗渊源及其对中古波斯文化的塑造。而从艺术角度看,帕提亚帝国为萨珊时期伊朗王权艺术形象的确立奠定了诸多核心元素,如从骑枪决斗和狩猎等题材均可发现萨珊艺术的帕提亚渊源。尽管帕提亚诸王留下的纪念性岩刻只得到部分保存,仍可以从中窥见帕提亚国王骑马征战、击杀敌人和从琐罗亚斯德教神祇手中接受神圣王权的形象。因此,不管萨珊帝国如何抹去帕提亚人的统治印记,也无法否定帕提亚人为萨珊王朝奠定的艺术表达方式,因为这就是萨珊王朝纪念艺术风格的直接来源。正如20世纪前期“希腊化”研究权威罗斯托夫采夫所指出的那样,“萨珊王朝初年丰富的纪念性岩刻与帕提亚时期同类作品的稀缺给后人留下一种假象——即萨珊人复兴了伊朗民族文化,而真实的情况是,萨珊艺术的支柱是帕提亚艺术,萨珊波斯人正是通过帕提亚人学会了波斯阿契美尼德艺术的核心表达方式。”
综上所述,传统学界强调的帕提亚王朝“希腊化”和“内亚性”特征对于揭示帕提亚帝国的文化本质而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希腊化”仅仅是帕提亚帝国文化万花筒中的一个光谱,而帕提亚帝国的“内亚性”则始终与波斯宗教文化传统中的“伊朗性”深度结合。“爱希腊”是帕提亚帝国前期的文化宣传手段和帝国政策工具,而承继自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伊朗性”特征则是帕提亚帝国的主流文化底色,并对萨珊王朝以降中古波斯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帕提亚帝国前期通过“希腊化”和“内亚性”的手段来表现自己的“伊朗性”,而帕提亚帝国后期则通过大力支持和直接复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统治观念和琐罗亚斯德教伊朗文化来明确表达对波斯传统的复兴。通过帝国前期的间接表达“伊朗性”和帝国后期的直接弘扬“伊朗性”,帕提亚帝国最终为萨珊帝国时期波斯文化的繁荣鼎盛奠定了有利的文化氛围。因此,在帕提亚帝国的文明交往进程中,“希腊化”虽然曾经风行一时,“内亚性”也看似鲜明突出,但“伊朗性”及以之为载体的古代伊朗族群、宗教与文化传统才是辨别帕提亚帝国文化属性的核心标识。帕提亚史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适度继承传统希腊化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伊朗文明自身历史发展规律,综合利用西方古典学、伊朗语言学、近东考古学和内亚研究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探讨帕提亚帝国对伊朗文明的继承、发扬与塑造。只有重新发现和阐释帕提亚帝国“伊朗性”的文化内涵、表达方式和演化逻辑,才能够正确评价帕提亚帝国对古代伊朗文明的独特贡献与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