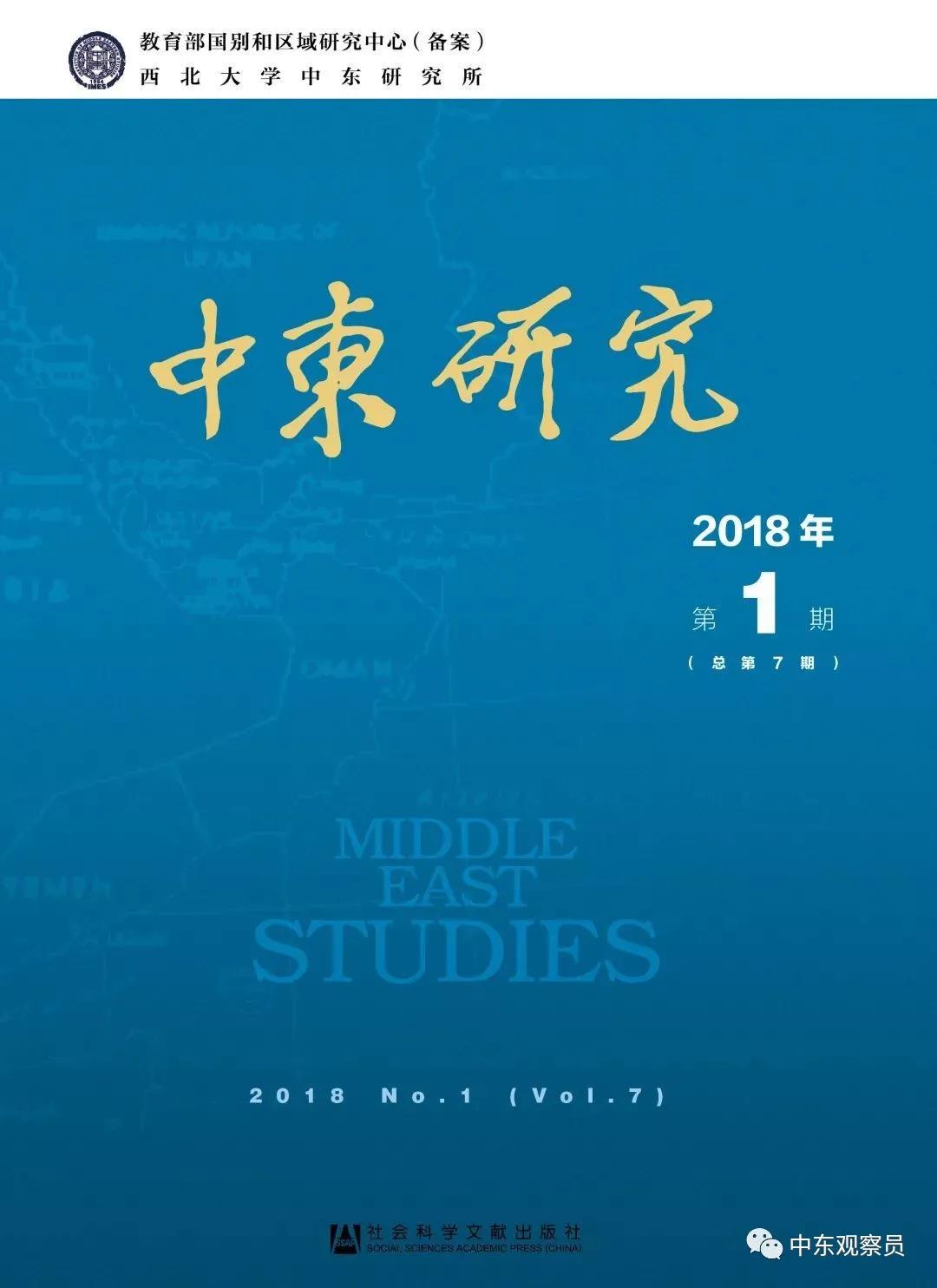
《中东研究》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主办的集刊,前身为1979年创刊的《中东资料编译》(内刊),入选CSSCI来源集刊目录(2021-2022)版。
欢迎关注公众号:中东研究集刊
文章来源:《中东研究》2018 年第 1 期
作者:龙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内容提要:萨法维王朝是伊朗高加索战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也是高加索地区博弈格局从古代的西亚二元对抗向近代 “俄国—奥斯曼—伊朗”三角博弈过渡的时期。在伊朗历代王朝中,萨法维王朝与高加索地区的关系最为复杂密切,影响也最为深远。此时,高加索首次成为伊朗对外交往的重要舞台和中介地区。沙皇俄国逐渐加入与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在高加索的博弈,成为近代高加索的第三个域外大国并日渐发挥重要作用。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对高加索的争夺构成 16 世纪西亚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并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萨法维王朝的对外政策。萨法维王朝的衰亡开启了俄国南下高加索并主宰着一地区的历史。近代伊朗与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争夺奠定了现代高加索的地缘政治、宗教和民族底色,并成为现代高加索地区持久动荡的历史根源。
关键词:萨法维王朝 高加索地区 奥斯曼帝国 国际关系
图片为本号编者添加,图源网络。

在现代地缘政治学研究中,高加索地区、欧洲的巴尔干、南亚的克什米尔地区并称世界三大地缘政治破碎地带。三者均以民族、宗教的多元性和政治格局的脆弱性著称,而高加索地区表现尤为显著。现代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民族和宗教格局与历史上外国势力的交替渗透、争夺和统治密切相关。在这里本土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并有抗拒外来强权的传统,而外部大国时刻不忘对该地区施加影响并谋求霸权。历史上各大国如何围绕高加索地区展开博弈并形塑现代高加索政治格局值得学术界深入探讨。然而,学术界一般将高加索地区的研究归为俄罗斯东欧研究的范畴。此归类方法以近代俄国在高加索地区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为历史前提,但却忽视了俄国势力介入前高加索地区政治历史演化所具有的西亚属性。即使在当代,高加索地区依然保留了来自西亚的强烈政治和宗教影响,其中宗教的影响不可忽视。高加索地缘宗教格局的特点引人注目,伊斯兰教在高加索与东正教分庭抗礼,同时自身又明显分为东高加索的什叶派和北高加索的逊尼派两大派系。不仅如此,两大教派内部又被众多支派相互制衡,各派在地理分布上也呈现犬牙交错之势,这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堪称罕见。高加索地区宗教底色的 “马赛克”式分布的历史根源值得研究。
现代学者已经注意到历史上博弈高加索地区的主要参与者有二: 一是以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东地中海大国; 二是东欧平原上兴起的沙皇俄国。而学界对伊朗在高加索地区的历史作用还未得到强调、梳理和充分研究。实际上,历史上伊朗是高加索地区博弈的最重要参与者,也是在该地区拥有最长时间政治影响力的国家。高加索地区地缘格局的破碎性肇始于古代伊朗诸王朝与 (东) 罗马帝国的争夺,延续至近代伊朗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争夺。俄国势力只是在 18 世纪后才开始进入高加索地区并最终在 19 世纪取代前者的地位。在 19 世纪彻底失去高加索地区之前,伊朗对高加索地区政治形势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始终无法成为该地区唯一主导势力。包括伊朗在内的高加索周边大国长期角逐于此,遂形成高加索地区复杂的利益结构和反复无常的政治归属变化。高加索地区的得失攸关伊朗国家西疆安全,是伊朗历代王朝盛衰的晴雨表。研究历史上伊朗国家对高加索地区的战略演变,对解析高加索地区破碎政治格局的历史根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对伊朗历史研究而言,伊朗国家高加索地区战略的演变是解读近代伊朗民族国家构建、对外关系和版图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萨法维王朝在近代伊朗国家由伊斯兰帝国 (Islamic Empire)向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转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萨法维王朝与高加索地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渊源,意味着研究伊朗国家高加索战略的变迁无法绕开萨法维王朝这一重要时期。
对萨法维王朝高加索战略的研究离不开对伊朗历史及对外关系,尤其是伊朗国家安全形势和西疆战略的历史考察。高加索地区自古以来便是西亚帝国争霸中心。古代波斯诸王朝经营高加索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6 世纪。近代伊朗萨法维王朝 (1501—1722) 自高加索地区兴起后,该地区在伊朗国家西疆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萨法维王朝对抗奥斯曼帝国的一线战场,高加索地区的得失与萨法维王朝的兴衰呈现出极为密切的联动性。同时在近代沙皇俄国兴起的大背景下,伊朗国家与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的二元对抗格局正逐步向 “伊朗—奥斯曼—俄国”三角博弈格局过渡。但是在萨法维王朝时期,俄国对高加索事务的影响力还未得到充分体现,俄罗尚不足以取代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力量,仅在后两者的博弈中发挥第三参与者角色的作用。但是萨法维王朝灭亡后仅数十年时间,俄国便一跃成为三方博弈中的最强有力者,并最终实现对高加索地区的完全征服。萨法维王朝灭亡前后高加索地区博弈态势的剧变和三国实力消长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高加索对近代俄、土、伊三国的战略意义不尽相同,但三国都把高加索地区视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巩固帝国霸权的重要基石。
对伊朗而言,高加索地区是西北边防重地,也是萨法维王朝对外战略的首要考量,更是其打开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孤立局面、联系欧洲国家制衡奥斯曼帝国的关键地缘节点。对奥斯曼帝国而言,高加索地区是其环黑海霸权的重要屏障和依托,也是其对萨法维王朝长期保持战略优势的地缘支撑。而对俄国而言,高加索地区既是其实现南下印度洋战略的必经跳板,又是自身南疆安全的 “柔软下腹部”。由此可见,高加索地区对近代俄、土、伊三国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均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对近代三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博弈特征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对伊朗历史研究而言,高加索地区集中了伊朗历史上相当比例的涉外交往和冲突,成为伊朗国家发挥地区影响力的重要舞台。而萨法维王朝高加索战略的变迁也集中体现萨法维王朝时期伊朗对外交往与冲突特征,且与历代伊朗王朝高加索战略一脉相承。高加索地区的得失映照出伊朗国家荣辱兴衰的历史画卷,对伊朗民族心理和国家战略定位有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因而对萨法维王朝高加索战略的研究对理解伊朗国家安全理念、大国抱负和外交秉性的历史生成至关重要。最后,萨法维王朝作为近代伊朗民族国家复兴载体,其起源具有浓厚的 “高加索色彩”。萨法维王朝如何实现从土库曼部落国家 ( Tribal State) 到波斯土著王朝 (Native Dynasty) 的革命性转变,也需要从萨法维王朝对高加索地区的战略演化分析中求得解答。
国外学者对萨法维王朝对外关系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罗杰·萨沃伊的 《萨法维王朝治下的伊朗》等著作对萨法维王朝在高加索地区与奥斯曼帝国的百年征战进行了详细论述,但尚未从整个西亚—东欧地区国际体系的视角深入探讨高加索地区在萨法维王朝的战略地位。国内学者注意到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在近代早期中东历史上的重要性,从民族国家构建以及宗教意识形态等层面探讨了两者的关系,但并未深度挖掘导致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冲突的地缘因素,也未揭示出两国高加索博弈的历史继承性、过渡变革性以及对现代高加索地缘、民族、宗教格局的形塑作用。
本文以对伊朗国家历史发展和对外战略变迁的纵向历史考察为基础,以 16 ~ 18 世纪萨法维王朝高加索战略的演变为基线,系统考察高加索地区在伊朗国家边疆和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以期从伊朗国家和高加索地区的历史互动中梳理近代伊朗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地理线索和战略驱动,并对现代高加索地区破碎权力格局和动荡安全形势的历史根源做出尝试性解读。

一、古代遗产与 “龙兴之地”:
萨法维王朝与高加索地区的历史渊源
伊朗对高加索地区的国家经营有着久远的历史。公元前 6 世纪米底王国(前 671 ~ 前 550 年) 首次统治了外高加索地区。阿契美尼德王朝 (前 550 ~330 年) 继承米底王国建立波斯帝国后,在外高加索亚美尼亚地区设行省。帕提亚和萨珊王朝时期 (前 247 ~ 651 年),经过与罗马帝国的反复争夺,最终于公元 4 世纪末分得亚美尼亚东部。5 世纪初萨珊王朝在北高加索打尔班关 (Derbent,今译杰尔宾特) 建成要塞,自此确立了伊朗国家对整个高加索东部地区的统治。651 年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所灭,标志着古代伊朗国家对高加索东部地区统治的中断。但阿拉伯帝国本身继承了萨珊王朝的疆域,也接管了后者在高加索东部地区的大部分势力范围。阿拉伯帝国基本控制了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地区,其间伊斯兰教的渗入使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宗教格局进一步复杂化。阿拉伯帝国时期在外高加索地区的统治以间接统治为主,到了帝国后期当地土著已经获得相当程度的自治权。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落瓦解,9 世纪亚美尼亚王国得以再度复兴,同时又从亚美尼亚分化出了新兴国家格鲁吉亚 (Georgia,978)。后者于 11 ~ 12 世纪时曾一度十分强盛,多次成功击退塞尔柱突厥人。但中世纪以格鲁吉亚为代表的高加索土著国家已经难以恢复古代亚美尼亚王国时期的西亚强国地位,实际上是在西亚各大王朝的夹缝中生存。
11 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大批向外高加索和小亚细亚地区迁徙,迫使亚美尼亚人迁徙至地中海北岸的西里西亚 (Cilicia,即所谓 “小亚美尼亚王国”)。再加上 13 世纪蒙古西征引发的第二波突厥人迁徙浪潮,至 14 世纪外高加索地区已经聚集了大量突厥部落,从而构成了阿塞拜疆地区的主要民族。外高加索西侧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更是早在 11 世纪就完成了突厥化进程,而一度称雄于外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王国在经历蒙古和帖木儿入侵后彻底分崩离析。因此到了中世纪后期,高加索本土王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相继衰落,突厥民族和伊斯兰教分别大量进入和传入高加索地区已经成为无法扭转的历史趋势。并由这些突厥部落完成了构建近代伊朗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其标志便是 1502 年从外高加索东部阿尔达比勒 (Ardabil) 地区兴起的萨法维教团率领土库曼部落军攻占大不里士 (Tabriz) 建立萨法维王朝。
萨法维王朝建立后,统治者无论是从继承古代伊朗高加索遗产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稳固王朝发家的 “龙兴之地”出发,均要求对高加索地区取得绝对统治权。因此萨法维王朝以后,对高加索地区的经营成为伊朗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高加索地区的得失与近代伊朗诸王朝的盛衰从一开始便具有紧密的联动关系。
二、从战略放弃到强势回归:
萨法维王朝对高加索地区的战略变迁
高加索地区的丧失酿成 16 世纪萨法维王朝的生存危机。1502 年萨法维王朝建立后,伊朗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形势。中亚的乌兹别克昔班尼王朝 (1500 ~ 1598) 和奥斯曼帝国从东西两侧严重威胁着萨法维王朝的统治,其中尤以奥斯曼帝国对伊朗西部边疆的威胁最为严重。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初,奥斯曼帝国尚未征服埃及马穆鲁克王朝 (1250 ~ 1517),双方的总体国力对比以及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实力对比基本对等,这使得萨法维王朝统治者误以为可以重演当年帖木儿帝国于 1402 年在安卡拉 (Ankara) 大败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萨法维王朝开国君主伊斯玛仪一世 (Ismail I,1501 ~1524 年在位) 极力推动奥斯曼帝国东部边境信奉什叶派的土库曼部落向萨法维王朝倒戈,一度严重威胁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统治。虽然萨法维王朝这一时期在外高加索和东安纳托利亚地区利用其什叶派意识形态采取激进的扩张政策,但却没有政治军事力量的跟进。
萨法维王朝统治者低估了奥斯曼帝国采取军事报复的能力很快带来严重的后果。伊斯玛仪一世的频繁挑衅超过了奥斯曼苏丹塞里姆一世 (1512 ~1520 年在位) 所能容忍的底线,最终导致了奥斯曼帝国主动出兵进攻萨法维王朝。1514 年双方在乌尔米耶湖东岸的查尔迪兰交战,萨法维军队落后的部落骑兵在奥斯曼军队的火器面前不堪一击,首都大不里士随后陷落。查尔迪兰之战是萨法维王朝高加索政策的转折点,也是萨法维王朝整个对外政策的转折点。此战之后萨法维王朝统治阶层意识到自身综合国力和军事技术上与奥斯曼帝国的巨大差距,遂完全放弃了与奥斯曼帝国争夺高加索地区的野心。而奥斯曼帝国挟战胜之威兵锋南转,于 1517年征服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在西亚的实力对比从此更加悬殊,奥斯曼帝国随后连年入侵伊朗西部地区。1549 年塔赫马斯普一世 (Tahmasp I,1524 ~ 1576 年在位) 最终放弃位于外高加索前线的首都大不里士迁都伊朗高原腹地的加兹温 (Gazvin),便是萨法维王朝在西部边境对奥斯曼帝国采取完全守势的结果。1555 年双方签订的 《阿玛西亚和平协议》是对查尔迪兰战役以来双方关系的初步总结,此协议规定西阿塞拜疆和两河流域划归奥斯曼帝国,随后两国保持了 20 余年的短暂和平。
1576 年塔赫马斯普一世去世后,萨法维王朝政局动荡,奥斯曼帝国再次对伊朗萌生并吞野心。1584 年奥斯曼军队再次攻占大不里士,萨法维王朝由于国势衰弱只能听之任之。1587 年阿巴斯一世 (Shah Abbas I,1587 ~1629 年在位) 继位后为创造国内改革的有利环境,在 1589 年的 《伊斯坦布尔协议》中对奥斯曼帝国做出了巨大让步。协议规定包括大不里士、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地全部划归奥斯曼帝国,至此萨法维王朝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降到历史最低点。奥斯曼帝国虽然屡屡攻陷萨法维王朝旧都大不里士及附近地区,但由于萨法维王朝在阿塞拜疆地区实行的焦土政策,奥斯曼军队始终无法深入伊朗高原彻底征服萨法维王朝。因此在整个 17 世纪,萨法维王朝由于和奥斯曼帝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被迫放弃几乎整个外高加索地区,全力固守伊朗高原本土。尽管萨法维王朝通过以上措施避免了覆亡的命运,但奥斯曼帝国长期控制外高加索地区犹如高悬于伊朗国家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以凭借外高加索地区威胁萨法维王朝在伊朗高原腹地的统治。因此 16 世纪高加索地区的长期沦陷直接造成了萨法维王朝的生存危机。而当 17 世纪初阿巴斯一世改革基本完成后,收复外高加索地区便成为萨法维王朝实现中兴的必要条件。
收复高加索地区是萨法维王朝中兴的必要条件,但不足以保障萨法维王朝的长期稳定发展。17 世纪初萨法维王朝经过阿巴斯一世在内政上的中央集权措施和军事上利用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裔等非土库曼民族组建新军后,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于是收复被奥斯曼帝国长期占领的高加索各地区被提上日程。阿巴斯一世亲率新组建的近代化军队在 1603 ~ 1613 年屡次亲征高加索地区。1603 年阿巴斯一世在乌尔米耶湖一战大败奥斯曼军队,一举洗刷了当年查尔迪兰之战的耻辱。随后又相继收复了高加索地区的重镇大不里士、占贾、埃里温、第比利斯、巴库和杰尔宾特。1613 年,屡战屡败的奥斯曼帝国被迫与萨法维王朝签订 《伊斯坦布尔和约》,规定奥斯曼帝国放弃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和伊朗西部诸省,两国边界维持苏莱曼一世时期的状态,从而初步确立了阿巴斯一世的战果。
1616 年奥斯曼帝国不甘心失败,发兵企图夺回高加索东部,并于 1618年兵抵大不里士。在伊朗守军的顽强抗击下,奥斯曼帝国军队最终铩羽而归。通过 1618 年的 《埃里温条约》,萨法维王朝再次确保了 1613 年 《伊斯坦布尔和约》中获得的高加索东部地区,并在此条约中将高加索西部的格鲁吉亚收复。至此,萨法维王朝经过和奥斯曼帝国长达一个世纪的争夺,最终完全收复了包括北高加索的杰尔宾特,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大部分高加索地区,萨珊王朝时代的西北边境线得以重新确立。萨法维王朝虽然在经过艰苦争夺后收复整个高加索,但却未能长期巩固对两河流域的统治 (萨法维王朝仅在 1508 ~ 1534 和 1624 ~ 1638 年短暂占有两河流域)。1639 年的 《席林堡和约》签订后,萨法维王朝便永久放弃了对两河流域的主权。因此,阿巴斯一世的征战结果虽然极大地振奋了伊朗国家的民族精神,甚至在欧洲各国广为流传,实际上萨法维王朝通过收复高加索地区远远不能达到消除奥斯曼帝国潜在威胁的目的,仅仅是在约一个世纪内 (1618 ~ 1722) 确保了伊朗国家的国防安全。由于奥斯曼帝国仍然占据两河流域,萨法维王朝在西亚仍无法对奥斯曼帝国取得绝对优势。一旦萨法维王朝衰落,奥斯曼帝国势必卷土重来,萨法维王朝苦心收复的高加索地区将再次成为一线战场。由此可见,高加索地区是立足于伊朗高原政权生存所必需的必要安全区,但却远不足以成为王朝生存的充分安全区。
三、 “中兴福地”与 “外事之窗”:
萨法维王朝以高加索地区为依托实施 “远交近攻”战略
高加索地区是 16 ~ 17 世纪伊朗与欧洲国家交往的重要窗口,是萨法维王朝远交近攻政策的地缘联结点。萨法维王朝统治者对高加索地区的心态是十分复杂的,高加索地区对萨法维王朝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力。高加索地区既是王朝龙兴之地,又是长期抗击奥斯曼帝国的前线,也是阿巴斯一世军事改革组建新军的关键兵源地。不仅如此,高加索还是当时伊朗与西方国家取得联系的几乎唯一通道,是萨法维王朝实施远交近攻政策的地缘联结点。由于奥斯曼帝国阻断了萨法维王朝通过地中海和欧洲国家建立联系的传统路线,萨法维王朝只能经由高加索东部和里海西岸地区绕道俄国,并以俄国为中介和西方国家建立联系。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也必须以俄国为中介取道高加索地区进而和萨法维王朝取得联系。早在 1553 年英国商人便获得沙皇伊凡四世 (1533 ~ 1584 年在位) 的特许,建立了以俄国为中介谋求与伊朗进行蚕丝贸易为主要目的的莫斯科贸易公司。1561 年该公司总经理安东尼·金肯森亲自率团由俄国取道高加索进入伊朗,并呈上英王伊丽莎白一世 (1558 ~ 1603 年在位) 的亲笔信。
1567 年莫斯科贸易公司又派出代表团取道俄国和高加索访问伊朗,并最终使塔赫马斯普一世同意英国商人在伊朗自由经商。但由于在整个 16 世纪萨法维王朝对高加索地区的统治形同虚设,莫斯科贸易公司两次来伊进行贸易接触所取得的成效极为有限。因为萨法维王朝此时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欧国家通过俄国和高加索地区 (奥斯曼帝国实控) 对伊朗进行非官方的主动接触。而且由于奥斯曼帝国此时拥有对整个高加索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西欧国家即使借道俄国和高加索仍无法和伊朗进行官方的外交接触。这种局面只有到 17 世纪初萨法维王朝收复高加索地区后才得以打破。在 17 世纪高加索沦陷期,萨法维王朝可以拉拢的反奥斯曼帝国盟友除俄国外寥寥无几。即使寻求和俄国结盟也受到 16 世纪末俄国动乱局势和奥斯曼帝国的极力阻挠 (伊朗出使俄国的使团经过高加索地区时曾多次被奥斯曼军队攻击)。俄国沙皇尽管在双方来往信件中多次表达出帮助伊朗的意愿,但在整个 16 世纪未发一兵一卒响应萨法维王朝联合攻击奥斯曼帝国的请求。17 世纪初,萨法维王朝的远交近攻政策的实施得到统治者在高加索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跟进和支持,从而保证了萨法维王朝对外交往的效力。萨法维王朝对欧洲国家关系的突破口起自 1598 年英国贵族安东尼·雪利和罗伯特·雪利兄弟趁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停战间隙,经东地中海奥斯曼领土,抵达萨法维宫廷。雪利兄弟不仅帮助阿巴斯一世建立起一支由高加索裔居民为主力的近代化火器军队,还推动他向欧洲各国派遣外交使团,成为萨法维王朝远交近攻政策实施的真正开端。
1599 年,安东尼·雪利和侯赛因·巴亚特率团从伊斯法罕出发访问欧洲各国,此次出使采取的便是高加索—俄国—西欧路线。使团先后抵达俄国、神圣罗马帝国、罗马教廷和西班牙宫廷,最终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积极响应。后者立即派出使团经俄国回访伊朗。而为确保使团归国路线的通畅以及建立萨法维王朝在欧洲的影响力,阿巴斯一世亲自率领新军秘密西进高加索前线以配合伊朗使团在欧洲各国的外交结盟工作。1603 年 12 月神圣罗马帝国的回访使团抵达伊朗边境,与此同时阿巴斯一世成功突袭奥斯曼军队收复大不里士。萨法维王朝在高加索的军事胜利对伊朗与俄国、神圣罗马帝国成功缔结反奥斯曼同盟起到了关键作用。
1604 年俄国立即出兵帮助伊朗军队围攻北高加索的杰尔宾特,同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同意缔结伊、俄、神罗三国联盟,萨法维王朝的远交近攻政策至此取得了初步的成功。1608 年阿巴斯一世再派罗伯特·雪利取道高加索出使欧洲,先后到达波兰、德国、罗马教廷、西班牙和英国宫廷,最后经非洲好望角,回访印度莫卧儿王朝后,于 1614 年回到伊朗。雪利兄弟两次经高加索地区出使欧洲,使得欧洲各国了解到阿巴斯一世在高加索前线对奥斯曼帝国取得的一连串重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萨法维王朝在当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虽然欧洲各国并没有给萨法维王朝太多实际上的支持 (只有俄国短暂出兵),但欧洲各国的声援无疑为阿巴斯一世坚决收复高加索地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因此,在 17 世纪初萨法维王朝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相互配合,以武力收复高加索地区为后盾,支持雪利等人经高加索地区出使欧洲的外交工作,使萨法维王朝的远交近攻政策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萨法维王朝得以凭此在近代伊朗历史上取得后世无法复制的辉煌地位。
四、从二元对抗到三角博弈:
萨法维王朝灭亡前后高加索地区国际关系的剧变
萨法维王朝时期高加索博弈格局开始由 “奥斯曼—伊朗”二元格局向“俄国—奥斯曼—伊朗”三角格局转化。萨法维王朝处于国际体系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关键时期,而 16 ~ 17 世纪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博弈过程在传统逻辑中也蕴含着新的变革性因素。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频繁争夺高加索地区,从本质上看是古代伊朗诸王朝和罗马帝国在高加索博弈的延续,此地的得失仍主要取决于伊朗和东地中海国家的实力。
由于长期控制两河流域和环黑海地区,奥斯曼帝国在整个 16 世纪的高加索博弈中占据绝对优势。即使在 17 世纪初丧失高加索大部,仍然保留了随时卷土重来的实力。而萨法维王朝始终无法打破奥斯曼帝国对东地中海交通贸易线的垄断,只能借道高加索和波斯湾与西方国家取得联系。这种联系尽管具有突破性的历史意义,但无法从根本上挽回伊朗在西亚历史上曾长期拥有的丝绸之路中介国地位。收复高加索实际上仅能解决萨法维王朝的生存问题,但无法解决萨法维王朝的发展问题。萨法维王朝一度繁盛的蚕丝贸易由于陆路交易成本远高于东地中海地区和新航路,在 17 世纪下半叶很快衰败,进而掐断了萨法维王朝赖以生存的关键财源。萨法维王朝由于奥斯曼帝国的阻隔未能成功融入地中海贸易圈,也无力角逐英、荷、西、葡等西方列强争夺新航路的控制权,因此实际上仍被相对孤立于伊斯兰世界东部。
在 16 ~ 17 世纪,沙皇俄国通过于 1556 年吞并阿斯特拉罕汗国(1466 ~1556) 将国境推进至高加索山以北,自此成为高加索地区博弈的第三大外来势力。但在 18 世纪之前,沙皇俄国对外扩张的重点并不在此地区。终萨法维王朝一代,直到彼得大帝发起 “向波斯进军”之前,沙皇俄国和伊朗一直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俄国是伊朗和奥斯曼帝国对抗的重要外援。此时,沙皇俄国在高加索地区博弈中只是一个新的参与角色,但主导角色仍是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另外,此时沙皇俄国在黑海和高加索地区的扩张在客观上受到奥斯曼帝国和克里米亚汗国的阻碍。16 ~ 17 世纪,奥斯曼帝国与其在黑海地区的铁杆盟友克里米亚汗国 (1430 ~ 1783) 将黑海纳入其势力范围。克里米亚汗国不仅多次派兵帮助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进攻萨法维王朝,而且常年进犯沙皇俄国掠夺人口。沙皇俄国在 1783 年征服克里米亚之前,只能通过北高加索的陆上通道 (杰尔宾特和巴库) 进入西亚地区,在后勤保障上面临极大的困难。因此,在近代早期沙皇俄国的实力尚不足以在高加索地区的博弈中充当主导角色,对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在高加索的统治均不构成重大威胁。但是自 17 世纪中叶以来,来自沙皇俄国的哥萨克 (Cossack) 流民开始寇抄萨法维王朝的高加索和里海沿岸领地,萨法维王朝和沙皇俄国的关系在逐渐发生微妙的变化。随着 18 世纪初萨法维王朝的灭亡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俄国国力的上升和南下政策的出台,高加索地区的博弈格局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沙皇俄国最终将成为高加索地区格局的主导力量。
首先,俄国对高加索地区的野心由来已久,但俄国真正试图征服高加索始于彼得大帝(1682 ~1725 年在位) 时期。16 世纪,欧洲沙皇俄国的兴起和对东欧、中亚、西伯利亚金帐汗国一系列的后继国家的吞并使高加索山以北地区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强大政治实体。但直到 17 世纪中叶以前,沙皇俄国仅满足与控制顿河和伏尔加河下游一带,整个黑海东岸和里海西岸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在黑海地区由于奥斯曼藩属克里米亚汗国的阻隔而没有出海口,在里海沿岸的势力范围也仅限于杰尔宾特以北地区。因此在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前,俄国在高加索的势力远不及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对后两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利益不构成严重威胁。萨法维王朝在和奥斯曼帝国争夺高加索地区的斗争中,多次试图引俄国为外援,西欧国家也多次借道俄国经高加索地区和萨法维王朝进行的一定的外交接触。但总的来讲,16 世纪俄国在高加索地区博弈中处于次要地位,但已经能够影响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的对外政策,并在萨法维王朝的远交近攻政策中发挥了重要的地理中介作用。17 世纪初萨法维王朝收复高加索东部失地后,基本形成了和奥斯曼帝国分控高加索东西两部的地缘格局,且萨法维王朝控制了高加索地区相对较多的部分,有效解决了萨法维王朝面对奥斯曼帝国战略纵深不足的问题。1629 年阿巴斯一世去世后,奥斯曼帝国曾试图夺回高加索东部,但最终没有成功。至 1639 年 《席林堡和约》签订,高加索地区进入了较长的和平时期。但随着 1613 年俄国罗曼诺夫王朝(1613 ~ 1917) 的建立以及东欧平原上哥萨克人的兴起和对外扩张,萨法维王朝和俄国的友好关系开始出现裂隙。至 1682 年彼得大帝即位前,萨法维王朝和俄国的关系由于双方在高加索地区一系列的边境摩擦和哥萨克人在 17 世纪 60 年代对里海沿岸的大规模寇抄而变得极为冷淡。
其次,萨法维王朝的灭亡为俄国南下高加索提供了历史机遇,但俄国因各种因素牵制未能在彼得时代完成对高加索的征服。随着 18 世纪初彼得大帝在国内改革和欧洲方向上的战略成功,为俄国寻找南部暖水港口成为彼得大帝生前的最后目标,并贯穿以后历代沙皇的既定政策中,此即著名的 “南下政策”。而在彼得大帝时期,南下政策的突破口即已出现,18 世纪初,在阿富汗反叛部落打击下摇摇欲坠的萨法维王朝无疑成为俄国觊觎的对象。1722 年,萨法维王朝被阿富汗部落攻灭,早就对伊朗领土垂涎三尺的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立即联兵入侵伊朗西北部。1724 年俄奥签订 《伊斯坦布尔协议》瓜分了萨法维王朝在伊朗西部、高加索和里海沿岸的领土。但好景不长,1725 年彼得大帝去世,与此同时伊朗萨法维王朝旧部在后来阿夫沙尔王朝 (1736 ~ 1796) 建立者纳迪尔的辅佐下死灰复燃,阿富汗人、奥斯曼帝国在能征善战的纳迪尔打击下接连败退。俄国安妮女皇 (1730 ~1740 年在位) 审时度势,遂于 1735 年从高加索和里海沿岸撤走了全部的驻军。至此,18 世纪前期沙皇俄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初步军事征略以失败告终,但此次军事行动为后来俄国复入高加索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彼得大帝时代俄国之所以未能征服高加索地区,除了彼得大帝过早去世的个人偶然因素外,此时的俄国尚未打通黑海出海口是未能长久占领高加索和里海沿岸的根本原因。地理因素决定了俄国必须先吞并克里米亚取得出海口,才有能力向高加索方向快速投射军事力量乃至征服高加索地区,这最后被历史所证明。
最后,萨法维王朝灭亡后,俄、土、伊三国实力对比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发生了无法逆转的颠覆性变化,使得沙皇俄国能够在 19 世纪凭借其凌驾于伊朗恺加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实力真正征服高加索地区。通过对1722 ~ 1796 年三国历史发展的横向考察可以发现,俄国在三国中最早走出内部调整期并再度重启南下政策,而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均陷入无可挽回的国家衰退。彼得大帝在 1725 年的早逝一度使俄国陷入长达 30 余年的内部动荡期,至 1762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 (1762 ~ 1796 年在位) 继位前,俄国先后经历六位沙皇,平均在位不到七年。由于皇位更迭频繁且内部不稳,俄国在此期间基本停止了对外扩张。但 1762 年叶卡捷琳娜继位后,在女皇的励精图治下俄国迅速焕发生机,并于 1768 ~ 1774 年第六次俄土战争中彻底打败奥斯曼帝国。1774 年,俄奥签订 《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奥斯曼帝国从此丧失对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权。1783 年,沙皇俄国正式吞并克里米亚,奥斯曼帝国长达 300 余年的黑海霸权至此瓦解,而俄国则一举实现了夺取黑海出海口的战略目标。1785 年沙俄正式组建黑海舰队,从此大幅增强了在“黑海—高加索—里海”一线的军事投射力。
反观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均在国家改革或调整中遭遇重大挫折且陷入持续衰退。奥斯曼帝国在第六次俄土战争后一蹶不振,被迫在塞里姆三世 (1789 ~ 1807 年在位) 时期进行西方化改革,然而塞里姆三世的“新秩序”改革因为禁卫军政变而最终流产。在战场上奥斯曼帝国又先后于1792 年和 1813 年两度败于俄国,遂基本失去与沙皇俄国再次争夺黑海和高加索地区霸权的能力。伊朗在 1722 年萨法维王朝灭亡后,经过纳迪尔沙的十余年征战一度重新建立起强大国家,并成功征伐印度莫卧儿王朝、中亚诸汗国并在与奥斯曼帝国的较量中屡战屡胜,再次将北高加索杰尔宾特以南的高加索大部纳入伊朗版图。但由于阿夫沙尔王朝过分穷兵黩武,伊朗并未在国家建设上恢复萨法维时代的制度与文化活力,纳迪尔沙在北高加索的军事征略也因为当地土著列兹金人 (Lezgians) 的顽强抵抗遭遇重大挫折。1747 年纳迪尔沙遇刺身亡后,伊朗全境倒退至土库曼诸部落混战状态,并持续五十年之久。
1785 年恺加王朝建立后,经过开国君主阿加·穆罕默德的征战 (1785 ~ 1797 年在位) 勉强于 1796 年再次统一了伊朗全境,但此时伊朗版图由于阿富汗在 1747 年的独立建国而大幅缩水,从而极大地限制了恺加王朝的综合国力,而沙皇俄国的再度南下已经箭在弦上。1795 年,在俄国势力退出外高加索 60 年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再度出兵格鲁吉亚,与伊朗恺加王朝开国君主阿加·穆罕默德率领的波斯军队战争一触即发。只是由于两人先后于 1796 年和 1797 年去世,俄伊战争才被迫推迟至亚历山大一世 (1801 ~ 1825 年在位) 和法塔赫·阿里·沙 (1797 ~1834 年在位) 时期。在拿破仑战争 (1804 ~ 1815) 中,奥斯曼帝国和伊朗恺加王朝双双沦为欧洲列强博弈的筹码,并在与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战争中节节败退、丧权失地。1813 年俄国正式吞并格鲁吉亚,1828 年俄国在第二次伊俄战争结束后与伊朗签订 《土库曼恰伊条约》,从而获得了阿拉斯河以北的整个高加索东部地区。1877 年,俄国在第九次俄土战争中再度大败奥斯曼军队,俄国势力范围从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向亚美尼亚高原大幅推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在高加索再次交战,俄国军队深入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和凡湖一线,直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后,近代俄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征略基本结束。经过一个世纪的军事征服和蚕食,俄国最终在 “俄—土—伊”三国高加索博弈中胜出,将整个南北高加索地区纳入沙俄—苏联治下,从而开启了高加索地区的一元化时代。
五、承前启后、动荡之源与大国执念:
萨法维王朝高加索战略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后果
首先,萨法维王朝时期高加索地区国际关系的特征同时体现出历史继承性和过渡变革性。萨法维王朝见证了自古以来大国围绕高加索争夺博弈格局由 “二元对抗”向 “三角博弈”的转化。萨法维王朝的衰亡成为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确立主导权的前提条件。从总体上看,伊朗国家和高加索地区的历史互动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为 1~7 世纪,主要特征和表现形式为伊朗帕提亚王朝、萨珊王朝与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在高加索地区的战争交往。两大帝国均力图控制整个高加索地区,但最终伊朗占据了较大的优势,并确立起包括高加索东部地区的传统西北边界。但是两国长期对高加索的争夺对两大帝国的国力均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高加索归属问题直到萨珊王朝灭亡也未能彻底解决。
第二阶段为 16~17 世纪,主要特征和表现形式为伊朗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对高加索地区的争夺。奥斯曼帝国在 16 世纪表现出较大优势并控制了连同伊朗高原西北部在内的几乎整个高加索地区。而到 17 世纪又呈现出两国平分高加索地区的战略态势,实质是伊朗以失去两河流域为代价确保了在高加索东部的传统势力范围。在这一阶段俄国已经成为影响高加索局势的重要力量,但尚不足以成为主导高加索地区局势的力量。
第三阶段为 18~19 世纪,主要特征和表现形式为俄国经过数代沙皇的努力终于从奥斯曼帝国和伊朗手中夺取了整个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大部分地区。沙皇俄国从高加索地区博弈的 “第三方”一跃成为高加索地区第一大主导力量。俄国通过夺取高加索诸王国巩固了其在黑海和里海地区的优势地位,获得了进入西亚乃至印度洋地区的地缘跳板。而奥斯曼帝国和伊朗恺加王朝则由于和俄国在争夺黑海和高加索地区战争中的失利走上了衰亡与改革交替的近代化道路。萨法维王朝时代高加索地区博弈格局呈现出由 “伊朗—奥斯曼”二元博弈格局向 “俄国—伊朗—奥斯曼”三角博弈格局演进的特征。但此时俄国对高加索地区事务的主导能力尚不突出。18 世纪初,萨法维王朝自身的崩溃为俄国南下高加索创造了历史契机。但直至19 世纪俄国方才完成对高加索的征服,由此足见萨法维王朝对高加索地区的经营成果具有相当的持久性。
萨法维王朝时期高加索地区博弈的背后是传统西亚国际体系经历反复波折后逐渐向近代西方殖民体系过渡的过程。尽管萨法维王朝的高加索战略基本成功,但却无法扭转 18 世纪后西方国家全面向亚洲地区扩张的历史大势。随着 19 世纪与俄国战争的失败,恺加王朝放弃了萨法维时代在高加索的大部分遗产,仅保留了西北重镇大不里士及乌尔米耶湖周围地区。萨法维王朝的高加索历史遗产的丢失直接导致了现代伊朗西北疆界的形成,而现代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则基本由恺加王朝在与俄国战争中丧失的领土转化而来。因此,近代伊朗自萨法维王朝以降在高加索地区势力范围的收缩和俄国势力的南下共同奠定了现代高加索的基本政治格局。伊朗与古代罗马—拜占庭国家、近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经过千年高加索地区二元对抗博弈,最终在近代因沙皇俄国的强势介入而改变了高加索地区自古以来延续的西亚政治属性。高加索地区最终脱离了传统西亚国家博弈框架,成为俄国南进的前沿基地,进而被纳入俄罗斯—东欧国家体系,并由此塑造了现代高加索的地缘政治格局。19 世纪高加索博弈格局的剧变标志着高加索地区从此丧失了西亚地缘属性,成为以俄国为核心的东欧—中亚地缘板块的南部延伸带,一直到苏联解体高加索地区都是俄国的绝对势力范围。
其次,近代萨法维王朝及奥斯曼帝国对高加索地区的经营和争夺给高加索地区打上了难以抹去的伊斯兰化烙印。由于两大伊斯兰帝国分属逊尼派和什叶派阵营,使得高加索地区穆斯林教派归属也因为两国的争夺分别打上两大教派的印记。即使沙俄和苏联经过多年强硬统治也无法使高加索地区彻底去伊斯兰化,反而因为东正教的介入使高加索地区宗教结构更加复杂。现代高加索地区持久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基本来源于此。纵观高加索地区大国博弈的历史,伊朗在作为高加索地区博弈的重要参与方,和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等高加索域外强国一起,在高加索地区的历史演进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博弈贯穿高加索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也塑造了现代高加索地缘政治格局的基础。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伊朗国家保持了对高加索东部地区的强大影响力,但无法在整个高加索地区和所有历史时期占据优势。高加索地区的得失攸关伊朗国家安全和地缘利益,伊朗历代统治者均重视对高加索地区的经营。
尽管伊朗在近代最终失去了高加索东部地区的绝大部分,但伊朗国家在历史上对高加索东部的强大影响力仍然是现代伊朗在处理高加索地区事务时可资利用的无形资产。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现代伊朗和土耳其国家分别作为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开始对外高加索地区重新发挥政治、经济和地缘影响力。另外必须承认的是,由于高加索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强国均势争夺状态,客观上造就了现代高加索政治格局破碎化的历史悲剧。大国势力的交替统治和高加索地区尖锐的内部民族宗教矛盾共同导致了高加索地区对域外大国缺乏足够向心力的历史特性。一旦统治高加索地区的大国势力衰退,必然难以完全掌控地理和政治格局迥然不同的南北高加索地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失去了山南的外高加索地区,而北高加索地区由于地理上便于掌控没有脱离出去。但无论南北高加索地区,都存在着一系列困扰着当地民族国家和俄国的政治、宗教和民族问题 (如俄罗斯的车臣分离主义,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离主义以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卡冲突),高加索地区在现代仍然处于 “内弱外强”的政治格局。伊朗、土耳其和俄国仍然是影响当今高加索地区局势的三大域外强国,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三个高加索小国最终成为近代以来大国势力在该地区反复争夺后次第退潮留出的自然缓冲带。三个国家破碎化的疆界本身便是高加索地区千年来各大高加索域外强国进行反复激烈博弈在地理上留下的印痕。
最后,萨法维王朝高加索战略的演化充分阐释了历史上高加索地区对伊朗国家安全和王朝繁荣昌盛起到的支撑性作用。高加索地区得失见证了伊朗国家的历史荣败,成为近现代伊朗国家难以遏制其 “收复失地”冲动的重要根源。高加索地区在伊朗历史上是国家重点战略方向,攸关伊朗国家核心利益,起着屏障伊朗高原核心领土、维护伊朗国家安全的战略作用。而近代萨法维王朝在高加索地区势力范围及战略方针的演化与高加索地区国际体系的转型密切相关。自古代以降,高加索地区便是伊朗历代王朝的西北边防重地,古代波斯诸王朝和罗马帝国在此进行长期争夺,在近代又演变为伊朗、奥斯曼土耳其和沙皇俄国三方博弈的焦点。伊朗在 19 世纪以前的绝大部分历史时期均能有效控制以外高加索东部为核心的高加索大部分地区,而这无疑要归功于近代早期萨法维王朝对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奋起抗争和苦心经营。
纵观伊朗历史,萨法维王朝时期是伊朗国家对高加索地区经营力度最大的时期。萨法维王朝经过与奥斯曼帝国的百年争夺,最后确立了近代伊朗国家对高加索东部地区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萨法维王朝统治的稳固。萨法维王朝在不同阶段采取的高加索地区战略为萨法维王朝对内修整、对外交往和征战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但高加索地区本身无法保障萨法维王朝的长期地缘安全。俄国的兴起最初有利于萨法维王朝在高加索地区对抗奥斯曼帝国,但随着俄国、伊朗、奥斯曼帝国三国实力的消长,俄国最终成为伊朗西北边疆的真正威胁。自古代米底王国征服亚美尼亚高原并将外高加索地区并入伊朗国家版图以来,高加索地区作为伊朗国家固有领土的观念先后经过古代阿契美尼德王朝、萨珊王朝以及近代萨法维王朝和阿夫沙尔王朝的连续强化,形成了伊朗国家对包括北高加索东部在内的高加索东部地区作为伊朗传统西北疆界的基本认知。
然而,恺加王朝以前伊朗西北边界的形成是伊朗国家和古代罗马—拜占庭帝国和近代奥斯曼帝国反复争夺后的产物,其本身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伊朗西北疆界随着伊朗国家与东地中海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始终处于频繁的变动之中。伊朗国家力量强大时能较好地控制高加索东部地区,但却仅能保障伊朗国家在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腹地的安全。从古代罗马帝国到近代奥斯曼帝国均曾以高加索地区为跳板威胁伊朗高原腹地,以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东地中海大帝国是伊朗国家自古以来的宿敌。长期与强敌在高加索地区接壤和冲突使伊朗国家自古以来既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以屏障伊朗高原核心区,更缺乏心理上的安全感。从古代萨珊王朝到近代萨法维王朝,伊朗国家统治者均为打破高加索均势并扩大伊朗国家西北边疆纵深耗尽心血,但收到的效果却不甚理想。
伊朗与东地中海帝国在千余年的高加索拉锯战中帝国冲动逐渐减退,伊朗国家的高加索战略由古代恢复阿契美尼德王朝旧境的理想主义战略逐步转变为近代只图固守高加索东部地区的现实主义战略,同时完成了伊朗国家自身认知和定位由普世帝国 (Universal Empire) 向民族国家的转变。随着在恺加王朝时期东高加索地区的丧失,伊朗在高加索地区的领土仅余以大不里士为核心的南阿塞拜疆地区,近代伊朗国家借此完成了政治版图和伊朗高原地理疆界重新归位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讲,失去高加索东部虽然给近代伊朗带来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但客观上有助于现代伊朗民族国家的稳定建构。近代伊朗、奥斯曼帝国、俄国从高加索破碎地缘带的相继退出再次证明高加索地区虽然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被纳入帝国秩序,但终究会在域外帝国势力退潮后迎来民族国家分立高加索周边的现代政治格局。(注释略)